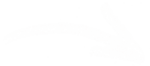放眼望去,这里如今空无一人、杂草丛生,很难想象半年多前这里还住着近万名难民。我回到加莱,想看看通往英国的隧道旁的非法难民营 "丛林 "被清理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站在山上,俯瞰昔日的营地,我想象着去年十月底的情景。营地有几处正在燃烧。乌云密布,浓烟滚滚。几名难民在抢夺最后的财物,而大批警察则在清扫现场。
当推土机准备将他们的家园夷为平地时,8500 名难民像一群动物一样被驱赶到一个临时作为分拣中心的寒冷大棚里。然后,他们被大巴车运往法国各地的城市。告别他们梦想中的 "英格兰"。
如今,难民营已荡然无存,仿佛不曾存在。昔日的居民将如何生活?我们不用等很久就能找到答案。在不到三条街以外的地方,在一些商业场所之间的空地上,我们发现了第一批难民。就像我们是来送食物的一样,我们一下车,第一批难民就向我们走来。
今天,我并非独自前往加莱。与我同行的还有鲍勃-里希特斯。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区。他不仅仅是去送一车捐赠物资。他想亲眼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
当天早些时候,我们驱车经过前难民营外几公里处的一个募捐棚。好心的志愿者在这里收集捐赠的食物和物品,然后分发给难民。塔高的物品被存放在这里。几名志愿者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们的到来;"出于安全考虑,大门一直关着。这些摄像机在这里做什么?不要拍摄这里的位置,我们过去曾遭到极右人渣的袭击"。
"鲍勃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没有提供任何工具,用这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确实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去年,我也看到了这种慈善活动的坏处。
许多志愿者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接受任务。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占据了不需要的权力地位,在很多情况下,除了贴膏药,他们缺乏更深层次的目的。今天又有食物了,明天还有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一名志愿者说,警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个地点分发食物,然后我们就得停下来" 鲍勃捐赠的物品每天可为 1200 到 1500 人提供食物。
鲍勃是一个小慈善家。在鹿特丹,他通过在三个地点开展的 "热点小屋 "项目,帮助许多人眼中的社会弱势群体。他的客户群包括瘾君子、无家可归者和一名被伊斯兰国灌输思想的女孩。"我的项目在根据需要不断发展,例如,现在有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在我这里活动,他们需要庇护所,所以我现在正在筹建一个热点小屋酒店"。"你知道 Michel,以家庭为基础的发展援助就是我的工作"。
在距离昔日 "丛林 "不到三个街区的地方,到处都是人。场地中央有人在打板球,我旁边一个几岁大的小男孩正踩着堆积的垃圾,还有一些人在睡觉。向我们走来的男孩中有一个来自厄立特里亚,我还认得他。他是我 10 月份在丛林里遇到的男孩之一。当时他在那里待了五个月,这意味着他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年。他看起来很疲惫,眼睛红红的。他用蹩脚的英语向我解释说,他在加拿大有个姐姐,姐姐会为他安排好一切。"我不需要再去英国了",他问我是否可以从中斡旋,我再次报出了我的电话号码,但我没想到她会给我打电话,还是不行。
该地区的难民称他们露宿街头。一些人说,他们受到警察的骚扰,"他们晚上来,拿走我们的物品,向我们的眼睛喷辣椒水"。有些人说,他们经常被抓起来,几个小时后才被释放。野外没有任何设施,包括水。
去年,我遇到了齐马科(Zimako),他是一名尼日利亚难民,2011 年大选后逃离了自己的国家。他为前政府工作的多哥父亲受到了威胁。通过利比亚和意大利,他最终来到了法国。与这里的其他人不同,齐马科不想去英国。他想留在加莱。
今天见到 Zimako 时,他已经长胖了,他来这里是因为要与 Bob 和 Veerle 见面。他们为他带来了洗衣机、烘干机和监视器。
在被驱逐之前,齐马科在丛林中的难民营里有一所学校。他辛辛苦苦建造的学校与丛林的其他部分一起被夷为平地。甚至在驱逐行动开始之前,齐马科就已经有了一个新项目,即为加莱的难民和居民开设一家洗衣店。现在,他还想开一家网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与去年不同的是,我怀念他说话时的自信。洗衣机、滚筒式烘干机和监视器最后都放在了公寓楼的地下室里,他在我的镜头前讲的故事,包括他的笑话,似乎都太照本宣科了。齐马科还是我去年写过的那个好人和地狱之门中的一线希望吗?是我太多疑了,还是因为荷兰的难民仇恨?
当我站在田边,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看着我的半包绒毛被分给十几个难民时,鲍勃向我走来。"Michel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解决办法吗?"我想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当我们驶过停在拐角处的警车时,我听到鲍勃对他随行的两个手下说:"定制化,逐一与他们接触,找出解决方案。"
我个人认为,加莱是我们欧洲和荷兰处理难民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没有解决问题,而是转移问题,假装一切都很好。我们继续重蹈覆辙。我们将难民隔离开来,创造出一个新的阶级,并分心讨论我们作为人类是否对另一个人负有任何责任。结果在 10 年或 20 年后才发现,这些新的荷兰人将反叛建制派。
而在我们这样做的同时,不仅加莱成千上万的难民露宿街头,等待着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