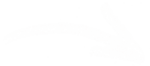我们有时会说,事后诸葛亮说起来容易。我同意,有时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作为一名以冲突和危机地区为工作领域的研究人员,我已经熟悉了不确定性和混乱,熟悉了不时面临的危险。在地球上一些最动荡的地区,我也曾成功地坚守过自己的岗位。然而,333 天前我遇到的敌人是我从未准备过的。这个盲人国度里无形的敌人,把我从熟悉的前线夺走,把我置于完全不同的前线:在未知的前线上度过了 333 天.
迷失在混乱中
我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与我曾经研究和报道过的地方恍如隔世。过去十年混乱和暴力的记忆在那一刻显得更加遥远。我刚刚给米特杰打了 "OK "的潜水手势,她也回了我一个手势,这意味着她能看到我,我还在那里。我的双手被柔软的 "手铐 "绑在床上,喉咙里有一条蛇使我无法说话。电缆和软管从我身体的不同部位连接到墙上哔哔作响的机器上。神志不清的时候,我会想象那些柜子里偶尔会有护士给我喂新鲜的卷心菜和其他蔬菜,他们在桌子上切下新鲜的卷心菜,然后通过小管子进入我的腹股沟,流进我的身体。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检查我的血液水平,看看是否需要添加更多的卷心菜或胡萝卜,在我神志不清的时候,我确实看到了更多与现实不符的东西。
潜水迹象表明一切正常,但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向 Mijntje 发出潜水的信号--一切都很好--现在回想起来并不那么明显。后来我才知道,事前看似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到了关键时刻却显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当这些决定涉及到你身边的人,而你必须在一个没有那么多保护的环境中做出这些决定,而不是边喝着美酒边愉快地交谈。只有到了后来,我才会明白,我这样做是多么地让别人为难。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我觉得谈论这个话题很困难。虽然我一如既往地努力公开这个话题,但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也很重要。我尽力而为,但也请大家理解。尽管如此,从这里开始。
梦想还是现实
住院头几天发生的许多细节,我要么没有想到,要么后来才想起来。直到后来,我才将这些细节拼凑起来。是谈话、病人的来信和一阵阵的回忆帮我拼出了这些拼图。我记得飞回荷兰、抵达机场、回家的片段。我还记得在全科医生那里,在医院里,我的胸口被重重地压了一下。我想我当时正用手和胳膊试图阻止别人再次按压我的胸部。后来我听说他们不得不对我进行人工呼吸。但如果你现在问我,我记得的是梦境还是现实,我可不敢把手伸进火里。随后的几天和几周是现实和幻觉的混合体--我不希望任何人有这样的经历。
我的身体很虚弱。就连坐直身子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仿佛像磁铁一样被吸附在病床上,连接在我身上的电缆和管子一天比一天少,直到最后连点滴都被拔掉,从我现在已经非常虚弱的手上取下。我想,几乎每个科室的专家都参与了我的治疗。我服用了几十种药物,但每天都感觉像是迈出了新的一步,有时甚至是一次胜利,无论多么微小。
我床脚的白板上列出了我的体重等信息。体重从 77.5 公斤开始,在短短一周内降至 62.4 公斤。这意味着有超过 15 公斤的液体离开了我的身体。虽然我的体重从来没有特别重过,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但在随后的康复过程中,我的体重会逐渐恢复到 80 公斤。
进步感和持久的斗争
有时,我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时,我就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据说是这样的:你会在不断的起步中取得快速进步,但康复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有些时候,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感觉自己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衡量的。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非常紧张。我每天都要接受物理和职业治疗、游泳、往返医院接受检查等等。
现在距离我濒临死亡已经过去 333 天了,我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回顾这段时光。不仅是住院的那段时间,还有之前的那段时间。在家接受了几个月的日间治疗后,一个半星期前我再次住进了康复诊所。三个月前的伤病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两星期前做了一次手术,几周后计划再做一次手术。如果一切顺利,手术后我很快就能进行康复治疗,回到 "受伤 "前的状态,然后继续治疗。
重新聚焦和前进之路
在康复的前六个月,我无法考虑工作。这仍然很困难,但在康复的同时,我正试图花一些时间寻找机会。目前,这将是在数字前线,因为坐轮椅很难到达其他前线。此外,我的身体状况还不允许我考虑离开。
前景相对较好,我希望能在三个月内看到更好的前景。有一点可以肯定,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我可能无法做到以前所做的一切,但它给了我新的启示,让我能够更好地做某些事情。我的生活将因此而永久改变。我将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身体,同时也看待我所爱的人,以及那些让生命更有意义的基本事物,有时这些事物我已经视而不见了。
在不久的将来,我将再次活跃于网络。我可能会偶尔写一些与你们通常习惯的我不同的主题,但我希望它们不会减少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