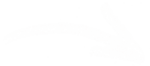我的美味甜点(Kunefe)刚吃了一半,政变的消息就传来了。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加济安泰普市中心外与两位医生讨论土耳其的医疗保健问题。主要是土耳其目前收容的 300 多万难民的医疗问题。
返回酒店
街道被关闭,桥梁被占领,战斗机和直升机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上空低空飞行。根据最初的报道。很快,我们决定结束谈话,各奔东西。
我被劝回旅馆。我决定去警察总部。我想,如果加济安泰普(距离叙利亚边境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即将发生什么事,那么在那里就能看到最初的迹象。我决定在警察局街对面一家封闭餐馆的楼梯上观看。
埃尔多安:走上街头
许多汽车高速驶向大门,人们忙着讨论。不多时,总理在电视上宣布政变正在进行。人们被要求走上街头,第一辆鸣笛的汽车出现在警察局前。人们举着旗帜,高喊着对埃尔多安总统的爱。顷刻间,整个城市似乎都在向市中心移动,道路变得拥挤不堪,人们一边呼喊一边继续步行。我决定离开警察局,跟随人群前往加济安泰普市中心广场。
当我到达中心广场时,广场上已经坐满了一半的人。埃尔多安刚刚表示政变已经失败,但也呼吁土耳其人走上街头和广场。广场上的人们疯狂起来,示威活动越来越具有真正的民众节日的特征。亲埃尔多安的城市加济安泰普也疯狂起来。
被攻击
前一天上午,我抵达加济安泰普,准备写一些关于土耳其和叙利亚的报道。我和广场上的其他人一样,没有料到会发生政变。我决定在翻译的帮助下与一些人交谈。尽管广场上熙熙攘攘,但一开始一切都很融洽。广场上的人们非常友好、开放和热情,就像我在过去几天里所了解的那样。我决定一个人在广场上转转,并想通过 Periscope 开启一个现场直播会是个不错的主意。在大约八分钟的时间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两个男人排成一条直线向我走来。当其中一人试图抢走我的手机时,另一人给了我第一拳。由于身边没有翻译,我试图解释我是谁,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第二拳就直奔我的眼睛而来。我试图跑向身后的街道,但被打翻在地,我站了起来,试图从停在街道上的汽车之间跑开。这时,两个人变成了五个人,我感觉又挨了一脚,突然发现自己倒在了两辆车之间。当一个男孩来到我和这些人之间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机会,迅速向酒店冲去。
我决定在当晚余下的时间里通过推特和电视关注相关信息。涌向市中心的人流似乎没有尽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变是否真的失败仍是个未知数,很快就出现了第一种说法,包括埃尔多安自己动手的可能性。凌晨 4 时 41 分,我决定该睡觉了。
派对继续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了受损情况;幸运的是,伤势并不严重。带着黑眼圈、一些擦伤和肋骨的不适,我决定在加济安泰普的中心广场重新开始新的一天。广场上依然人头攒动。人们似乎还没有离开,继续不知疲倦地狂欢着。
未遂政变发生前,原计划是去尼济普。尼济普位于加济安泰普以东一小时车程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难民营。我和翻译决定按计划行事。在满载货物的面包车里坐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尼济普。车外气温高达 41 度。
经过打听,我们很快发现今天几乎不可能去营地。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政府办公室关闭,营地也不对外开放。
在与几位已经找到住处的居民和前难民交谈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决定返回加济安泰普,看看中心广场的情况如何。埃尔多安呼吁人们留在街上;清真寺也通过扩音器重复这一呼吁。我的土耳其手机也收到了同样的短信 "到广场来,走上街头"。
再次受到攻击
在我离开的几个小时里,广场几乎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活动场所。广场中央矗立着一个高空平台,上面插着一面巨大的土耳其国旗。我被邀请使用高空平台的卡车从高空拍摄人群。当我走下高空平台时,四个愤怒的男人盯着我。我不知道他们在对我喊什么,我的翻译还在 AWP 的另一边。很快,一名警察站在了我的旁边,当他向我索要证件时,双方发生了冲突。我再次挨了几拳,并被推到了 AWP 上。警察让我跟着他们走。一名警察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向广场外的一个小岗哨。幸运的是,我的翻译看到了这一幕,并和我们一起走去与那名警官进行讨论。
在我们身后,节目的正式部分开始了。
政府雇员
很快,其他一些身着便装的政府工作人员也加入了我们。他们向我--主要是我的翻译--提问。我不得不交出我的装备、护照和记者证。他们通过对讲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命令。我后来从我的翻译那里得知,他们问她如何知道我和其他西方记者不一样,如何知道我可以信任,我们都做过什么,见过什么,和谁交谈过。
当特工翻阅我的手机,试图阅读我的信息并查看我的照片时,我努力回想我的手机里是否有任何罪证。我看到了一张叙利亚地图的照片,上面标注了当前的权力关系状况,我顿时咽了口唾沫,幸运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当时被一群从我们站的地方向大门走来的人分散了注意力。
一连串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文职政府官员来到这里,我的翻译被问得哑口无言。我完全听不懂发生了什么,只能相信最好的结果。
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官员知道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后来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现在,袭击我两次的这群人似乎属于一个仇恨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的团体。其中一名官员说,我们散布谎言或为其他政府工作。
他们现在认识你了,离远点
我的证件似乎没有问题,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获准离开。在我们获准离开之前,一位官员问我们为什么不向新闻办公室报告。在那里我可以得到帮助。这位官员说:'作为一名记者,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他还建议我不要再回到广场。你现在已经出名了"。
我决定违背这里的习俗和文化,去找啤酒喝。在酒吧喝了一两杯啤酒并与酒保聊了几句后,他决定我不应该独自回酒店。走出市中心的几个街区,街道上仍然挤满了按喇叭的汽车和大声喧哗的人群。我先前的狂欢感觉似乎变成了一种严峻、近乎恐怖的气氛。
酒保叫来了两个朋友。两个 "保安"。半小时后,我看到自己和那两个人穿过人群,向酒店走去。酒店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经知道了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很担心。他们比我当时还要担心。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在第二天前往加济安泰普南部与叙利亚交界的一个村庄--基利斯。当我们坐在开往基利斯的巴士上时,我的翻译向我们讲述了更多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边境村庄曾多次遭到来自叙利亚的火箭弹袭击。今年头五个月,至少有 20 名居民因此丧生。她有家人住在那里,他们将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天。
距离叙利亚五分钟路程
基尔斯人无所畏惧。不怕未来,不怕战争,什么都不怕。我从每个人那里得到的答案都是 "上帝会决定"。叙利亚人和土耳其人似乎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与我交谈的人中甚至没有人想到不再接纳难民。但政府似乎不这么认为。最近几个月,土耳其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修建了一堵高墙,收紧了入境规定,将难民与居民分开。例如,他们不能就这样离开难民营,长期难民只有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在城市之间旅行。
在一家茶馆里,我与几名叙利亚难民攀谈起来。其中一个是商人。他来这里已经六个月了,比一般难民享有更多的权利。例如,由于他的商人身份,他可以跨越边境往返。他向我提出,如果我的证件齐全,可以跟他一起走。谈话中,他提到了现代叙利亚的恐怖。在事件照片和视频的支持下,这位商人大声问道,作为欧洲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酒店前的警察
傍晚,当我回到加济安泰普的旅馆房间时,一辆警车停在了小旅馆的门口。两名警察下车走到前门。我可以发誓,他们说的是荷兰语。旅馆外,川流不息的人群涌向中心广场。就这样,我睡着了,希望今晚不会再有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