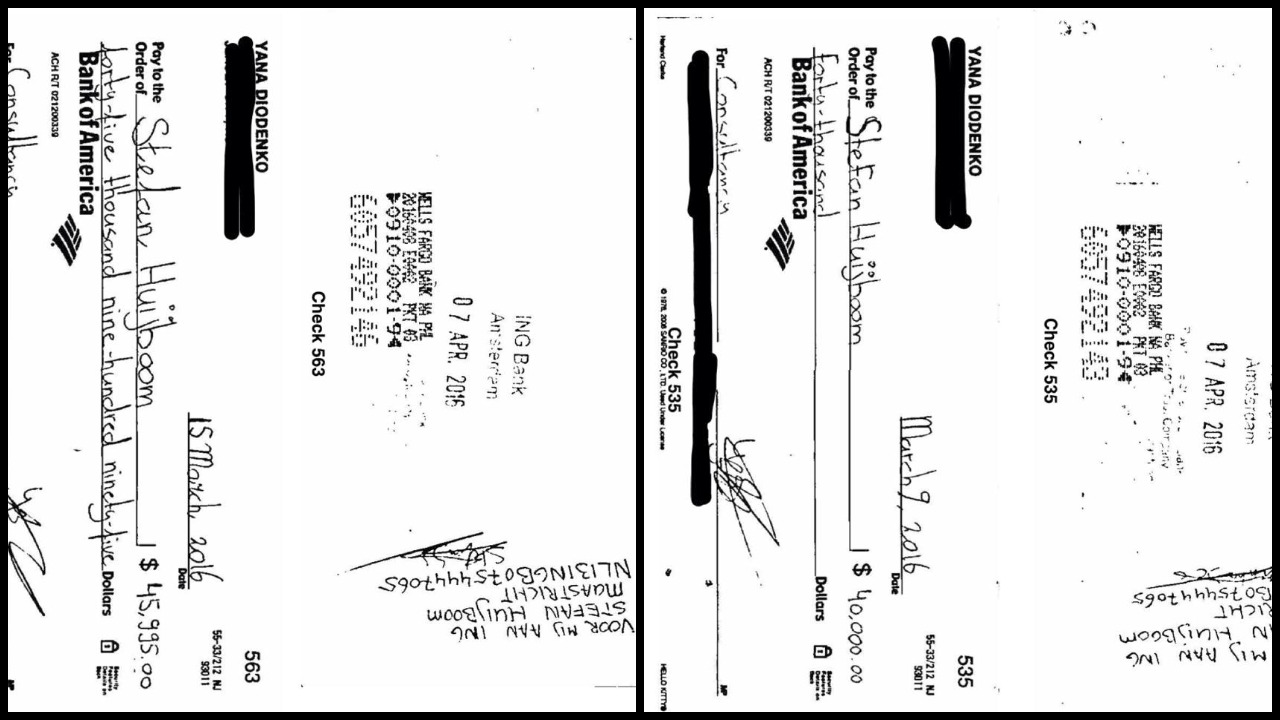最近几天,关于我决定将马航 MH17 遗体运往荷兰的消息甚嚣尘上。这是我的一面之词。
12 月 25 日星期日,我(与 Stefan Beck 一起)经华沙、莫斯科和罗斯托夫前往顿涅茨克。此行的目的(除其他事项外)是研究自 2014 年战争开始以来顿涅茨克民族革命军的日常生活和乌克兰东部的事态发展。关于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很多说法,其中许多说法相互矛盾。我们总共花了两个月时间进行准备,并考虑到包括安全在内的所有可能情况。
为什么通过俄罗斯。
最终选择了经俄罗斯前往 DNR。在一些人看来,另一条更合理的路线是经由乌克兰。自 2014 年以来,乌克兰东部一直在打仗。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承认 DNR。我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了解前线发生了什么,而是想看看居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以及 DNR 内部的政治发展如何。除了目前几乎不可能经由乌克兰前往该地区,而且也不可能获得新闻许可证之外,我们从(他们眼中的)敌对领土进入 DNR 地区并期待之后的合作也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在与俄罗斯领事馆和 DNR 内部的联系人等协商后,我们选择了俄罗斯路线。
参观马航 MH17 坠机现场。
鉴于我们只有有限的几天时间,参观两年半前马航 MH17 飞机坠毁的地点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列。头几天与当地几位人士的交谈让我决定调整行程,终究还是去坠机现场看了一天。斯特凡-贝克那天没有和我一起去。到达该地区后,我惊讶地发现有几处仍有明显可辨认的残骸。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带走一部分残片。其中大部分是铝、塑料零件和电路板。我想带走这些东西,目的是让他们接受调查,把它们交给有关部门,并有力地说明,2.5 年后仍然可以找到东西。在这些零件中,我发现了一些碎片,这些碎片让我强烈地联想到骨头残骸。早些时候发现的骨头残骸,其中一些被证明不是人类的,而是动物的。我不是法医,但不排除它们可能是人的遗骨。我考虑将其中一具遗骨带到荷兰作进一步调查。我的考虑是:如果这些是人类遗骸,那么它们就不属于这里,而应该带回荷兰。
随身携带物品
马航 MH17 的坠机地点距离顿涅茨克约 3 小时车程。那里有几栋房子和一家简单的急救商店。我决定将部分零件分别装在不同的袋子里。其中一块骨头我装在一个密封的管子里。后来返回时,所有部件都分别装在密封袋中。在整个旅程中,骨头部分都装在一个密封的硬容器中。我一整天都用胶片记录和拍照,包括物品、原地点以及我们遇到但没有带走的物品。我试图尽可能地记录所拍摄的物品。
鸣叫
令我感动的是,该地区仍有许多东西被随意丢弃。我无法想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荷兰,情况会是这样。我想起了吕特所说的 "底线",于是我发了一条现在看来非常不恰当的推特。
我最好把装满 MH17 东西的垃圾袋带给谁?....
- Michel Baljet (@michelbaljet) 2017 年 1 月 4 日
我的想法是:谁还在其中,谁就能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还是谁都不在其中了,让事情保持原样。发布推文后,我并没有立即得到疯狂的回应。在 EenVandaag 的一次广播中,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条微博在亲属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我立即为此道歉。
公诉
1 月 6 日,我收到了 Gerrit Thiry(马航 MH17 协调小组组长)的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表示希望尽快与我联系,'以便尽快将安全物品交由调查小组处置,以便在必要时进行法医调查'。 他还警告我,根据荷兰法律,从犯罪现场拿走物品属于刑事犯罪。同一天,我又收到了一封来自 Gerrit Thiry 的电子邮件,这是对我在接受 EenVandaag 采访时表示希望交出物品的回应。他在邮件中确认了我的愿望,并给了我两个移交选择:莫斯科联络处或史基浦机场。上周六,我们通过短信和电话相互确认了这是一次自愿移交,而不是刑事追缴。我们的航班延误了,我还是通知了他。到达史基浦机场后,我收到了他的短信,说他们会在登机口等我。
在海关
由于参观坠机现场那天斯特凡不在,他也不支持我带走骨头的部分,所以我们在飞机起飞前商定了一个坚定的告别。到达登机口后,格利特-蒂里和其他几位男士(包括一位数字取证专家和一些马雷夏赫协会的成员)对我表示欢迎。我们一起前往行李传送带领取行李。在行李传送带上,我的同伴拿错了行李,造成了短暂的混乱。不到一分钟,我设法(通过电话)联系到了他,并从他手中接过了行李。随后,我与 Thiry 和其他几位旅客一起前往史基浦机场内为我们预留的房间。Stefan 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直到一天后我才再次与他通话。
在房间里,甚至在移交之前,我就被问及数字取证专家是否可以制作我所有数据的 ISO(副本)。我随后表示,我愿意交出坠机现场的图像,但有一项谅解,即任何消息来源和对话都将匿名。我拒绝提供我在俄罗斯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整个行程中的所有数据,因为超过 90% 的数据与 MH17 无关,其中包含政治敏感信息。此外,我也不认为转移我的录音机和手机中的数据有什么意义,因为 0% 的数据包含了马航 MH17 的数据。对于我提出的仅限于马航 MH17 和坠机地点的数据的建议,检方立即表示不同意,随后他们开始没收我的所有物品。他们没收了我的一台笔记本电脑、3 部手机、一台 4k 松下相机、一台尼康 D80、一台小型摄像机、一台录音机、一个外置硬盘和几张 SD 存储卡。我请律师的要求被拒绝了。最后,我还是当着他们的面打了个电话通知了某人。
如何继续
我对事情的结果感到遗憾。我对检方的做法感到失望。我也完全不同意他们发布的新闻稿。我从第一天起就表示我想交出这些东西,我从未放弃过这一想法。我们可以争论道德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讨论的是,一些媒体平台和记者在没有互惠的情况下发表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这在最近几天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对 NVJ 的支持表示感谢。地方法官目前正在考虑扣押事宜。我已经申请了消息来源保护。我认为法官会批准消息来源保护,之后我仍愿意自愿交出相关录像。预计法官将于 1 月 10 日或 11 日做出裁决。
我要向马航 MH17 中遇难者的亲属致歉,既要为那条非常糟糕的推特道歉,也要为旧事重提的事实道歉。最近几天各种媒体的错误信息对此毫无帮助。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要问我,我随时都可以回答。
更新:Stefan Beck 的声明如下 这里
照片 弗拉迪斯拉夫-泽连伊)